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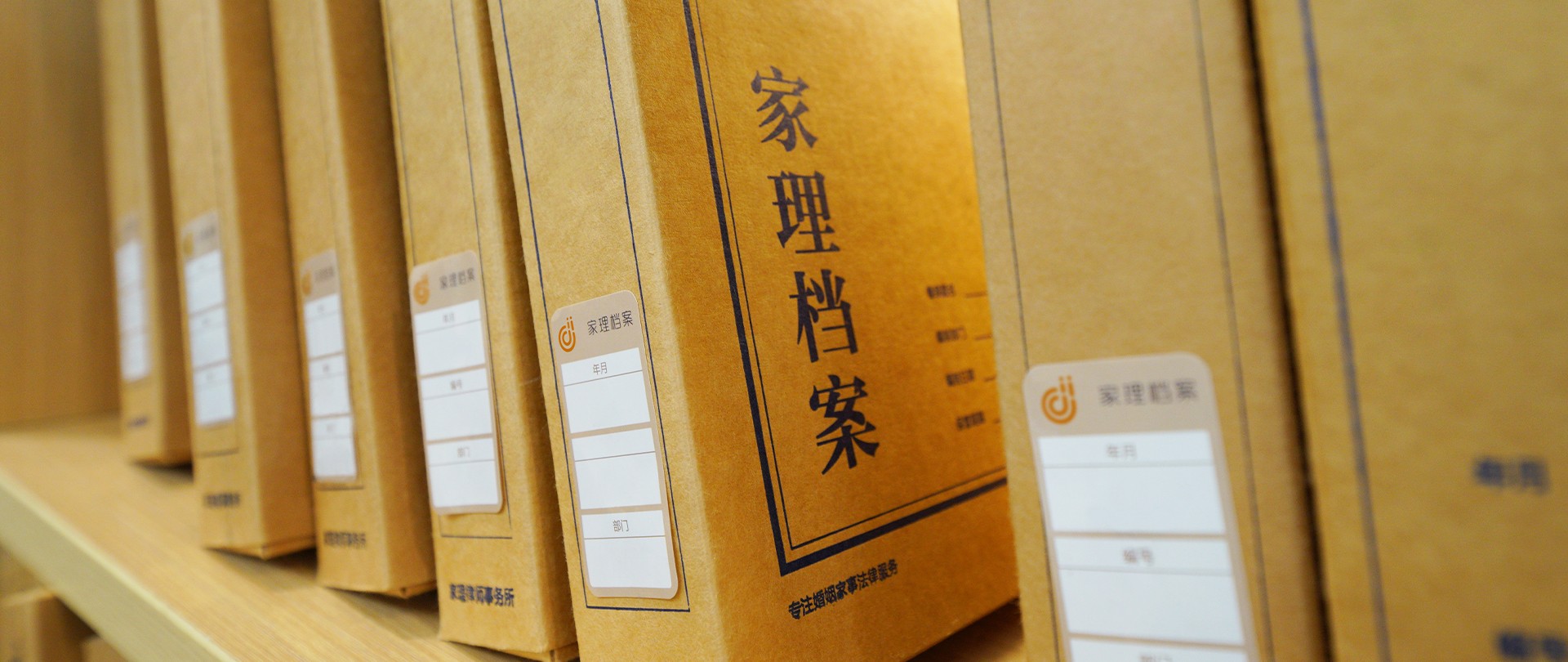
在法定继承纠纷中,若继承人以外的扶养人已获得高额酬谢,是否还能主张分割遗产?近日,家理律师代理的一起千万遗产继承案,对此给出了明确答案。2024年,赵女士(化名)在母亲去世后,突陷表姐提起的遗产分割诉讼,表姐已从赵母处获取330万元生前酬谢,又主张对千万元遗产(含房产及存款)享有50%继承权。赵女士虽为唯一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,却因“母亲早年缺席”的情感隔阂、不知如何梳理证据而束手无策。家理律师事务所高级资深律师赵冬雪、律师助理袁铭御介入后,从梳理关键证据、精准解读法律规定,到庭审中直击对方诉求漏洞,一步步帮赵女士厘清权利边界,一步步帮赵女士厘清权利边界,最终助赵女士获判90%遗产,让“借帮扶谋利”的诉求无处立足。
赵女士的成长历程中,母亲赵母长期处于“情感缺席”状态:因父母工作繁忙,赵女士自幼由祖父母抚养;10岁时,父母经法院调解离婚,赵女士被判由父亲抚养,此后赵母未履行抚养费支付义务,双方自此断联四十载。2020年前后,赵母再婚配偶及儿子相继离世,其曾试图通过亲属居中协调认回赵女士,却因早年情感创伤,未获赵女士回应。
2024年12月,赵母因病去世,表姐以“通知后事”为由联系赵女士。赵女士回京后,表姐交付遗物的同时,抛出了遗产分割要求:主张赵母失去家人后,自己承担了主要扶养责任(如陪诊、旅游、操办后事),应作为“继承人以外扶养较多的人”,与赵女士各继承50%遗产。
但赵女士通过亲属与银行流水确认:赵母生前已向表姐转账330万元——其中300万元是房屋出售后的“帮扶感谢费”,30万元为墓地续费款,且表姐庭审中也承认累计收到360万元(含30万元医疗费垫付回馈)。赵女士认为,母亲已用大额钱款对表姐的帮扶充分酬谢,其再主张分割遗产毫无道理;而自己作为唯一法定继承人,虽因母亲早年缺席未履行赡养义务,但法定继承权不应被随意剥夺。双方经亲属调解无果,2025年,表姐将赵女士诉至北京市法院,要求分割50%遗产。
此案因“亲属获高额酬谢后再主张超额遗产”的特殊性,法官坦言“属实践中少见情形”,先后四次组织调解均因双方分歧显著(表姐坚持50%份额、赵女士拒绝过度让利)未能达成一致。赵女士虽明晰自身法定继承人地位,却因“未履行赡养义务”的历史背景顾虑、证据体系构建能力不足,亟需专业律师介入打破僵局。
表姐的核心主张为“330万元属赵母无偿赠与,与酌分遗产无关联”,赵冬雪律师首要工作是构建资金流向与帮扶行为的关联证据链,证明酬谢已覆盖帮扶价值,再主张遗产分割属权利滥用:
固定大额酬谢证据:调取赵母银行账户流水,证实两年间,她先后向表姐转账330万元,其中30万元明确备注“墓地续费”,300万元为房屋出售后“感谢款”;结合表姐庭审中“承认收到360万元,含30万元医疗费回馈”的陈述,证明赵母已用远超一般帮扶的对价,对表姐的行为进行了酬谢,其再主张遗产分割属于“重复获利”;
弱化“扶养较多”事实:梳理表姐主张的“照料细节”(如陪看病、带旅游),发现多为偶尔协助(如挂号、短期陪同),而非长期固定赡养;赵母生前经济独立(每月退休金上万元,医保报销80%-90%)、生活能自理且雇有小时工,不存在“依赖表姐扶养”的情况,其帮扶远未达到“应分50%遗产”的程度;
证人证言强化事实:赵女士表妹出庭作证,称“赵母曾抱怨表姐推诿挂号”“2023年手术由护工照顾,非表姐”,进一步证实表姐的帮扶存在夸大,其诉求缺乏事实支撑。
表姐庭审中反复以“赵女士未履行赡养义务”为由,主张削弱其继承份额。赵冬雪律师从法律适用与事实溯源双维度出发,明确法定继承权的优先性,厘清“未赡养”的客观成因:
明确法定继承优先级:依据《民法典》第1127条,赵女士作为赵母唯一子女,是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,且赵母生前未立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,遗产本就应按法定继承处理;法定继承权不会因“未赡养”自然丧失,表姐主张“分走一半”,本质是试图突破法定框架,侵占赵女士的核心权益;
客观陈述“未赡养”成因:提交50年前的离婚判决书,证明赵女士自幼被判给父亲,赵母未支付抚养费且40年未相见——其“未赡养”源于母亲早年对抚养义务的缺席,及长期情感隔阂,并非“有能力却拒绝赡养”,主观无过错,不应以此苛责其继承权;
与法官深度沟通:强调赵女士的核心诉求是“维护法定权利”,而非“争夺财产”;表姐已获330万酬谢,若再分走1000万遗产,将彻底背离“权利与义务对等”原则,也会冲击法定继承制度的严肃性。
即便法院认可表姐存在帮扶行为,如何避免其获超额分割?赵冬雪律师通过量化测算帮扶合理价值、对比酬谢与遗产规模,为“酌分比例”提供客观依据,凸显50%诉求的不合理性:
测算合理酌分范围:赵母遗产合计约2000万元,表姐已获330万酬谢,远超一般“帮扶补偿”;结合其实际帮扶的频次与强度,主张“酌分比例不应超过10%”,既体现对善意帮扶的认可,又不损害赵女士的法定权益;
反衬50%诉求的荒谬:当庭指出,若按表姐主张分走1000万,加上已获330万,其实际获得将远超赵母遗产总额的60%,而作为唯一法定继承人的赵女士仅得40%,这既不符合《民法典》“法定继承优先”原则,也违背“权利与义务对等”的基本法理;
争取法官认同:强调“酌分遗产”的立法目的是鼓励亲属互助,而非让帮扶成为“投机工具”;表姐已获重酬,再高额分产会异化互助本质,最终法官采纳“10%酌分”的观点。
2025年,法院经审理后作出判决,全面支持家理律师的代理意见:
1. 赵母名下位于朝阳区的房屋,及银行卡账户内全部存款,均由赵女士继承所有;
2. 考虑到表姐对赵母有少量帮扶行为,赵女士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,向表姐支付遗产总额的10%补偿款
3. 驳回表姐要求“各继承50%遗产”的其他诉讼请求;
本案的典型性在于为“继承人以外的扶养人已获高额生前赠与,是否还能主张酌分遗产”这一实践难题提供了明确的裁判指引。家理律师的成功代理,得益于以下三大核心策略:
1. 证据闭环,切断“重复获利”路径
律师并未纠缠于情感争论,而是致力于构建坚不可摧的证据链闭环:通过银行流水锁定“330万重酬”事实,结合对方自认,证明生前赠与的价值已远超其帮扶付出。此举将案件焦点从“是否帮扶”转移至“是否应重复获利”,从根本上动摇了对方诉求的正当性。
2. 法理结合情理,稳固“法定继承”根基
针对对方“未尽赡养义务”的攻击,律师巧妙地将法律适用与历史成因相结合。一方面,援引《民法典》强调法定继承权的优先性和独立性;另一方面,用数十年前的离婚判决书客观呈现“情感隔阂”的背景,将“未赡养”定性为历史遗留问题而非主观过错,成功赢得法官的理解与支持。
3. 量化平衡,界定“酌分遗产”合理边界
面对法律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,家理律师主动提供量化计算方案:将已获酬谢与遗产总额、实际帮扶强度进行对比,科学论证对方主张的50%比例显失公平,并提出“不超过10%”的替代方案。这一策略将主观判断转化为客观分析,为法官提供了清晰且合理的裁判依据,最终被法庭采纳。
法定继承纠纷中,情感与法理交织。选择专业的家事律师不仅能厘清法律关系,更善于运用证据与技术手段,将抽象的情理转化为法庭上的有力论据,从而最大化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
赡养老人本是血脉亲情的自然延续,但当照顾行为被异化为财产争夺的工具时,便背离了孝道与互助的初心。本案中,表姐在已获330万元重酬后仍执意索要半数遗产,折射出当下部分亲属关系中功利性思维的蔓延。法律对赡养义务的保障与对法定继承权的保护,本质上都在维护家庭伦理的底线——《民法典》既赋予赡养义务强制性,也确认法定继承人的优先地位,正是为了引导家庭成员在真诚互助中寻求平衡,防止“待价而沽”的帮扶扭曲亲情本质。本案判决明确传递出这样的价值导向:亲属间的互助应源于真挚情谊而非利益算计,法律鼓励善意的赡养行为,但绝不纵容借“情谊”之名行“争产”之实。愿每个家庭都能以真心相待,让赡养回归亲情本源,让继承权成为家庭温暖的延续而非争夺的标的。